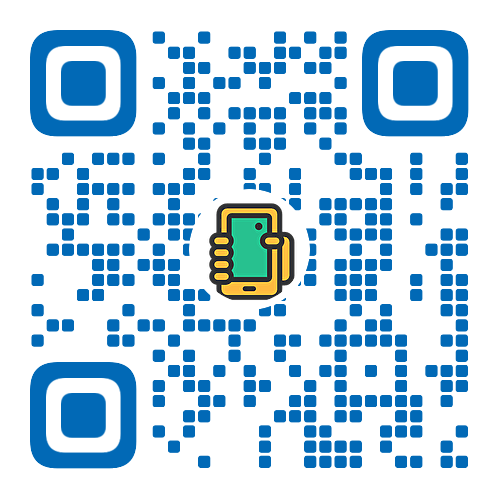滚动信息:
滚动信息:长篙
友人林火火出了诗集《我热爱过的季节》,承蒙青眼,签名相赠。虽然大多诗作己于QQ空间中见过,但是整理成册,铅印入卷,读来又是一番情境。
火火,为人爽辣。交往既久,常令人忘其年龄、性别,相互戏谑,仿佛赤子真人焉。前几年,骑行摔伤半月板,告别骑坛,塞翁失马也。又入文坛,不过二三年,竟与会诗刊“青春诗会”,公费出版诗集,焉知非福哉。
马鞍卸下,水笔提起,女性辛弃疾乎?
第一次被她诗歌吸引,在《木匠阿三》篇。短短十行,写尽了阿三的一生,令人拍案叫绝。视角独特:不写生活而生活自在,“缺了手指的阿三,在人群中失重,掉进厚重的自责里”,为什么是失重?为什么是自责,而不是愤怒或痛苦?人情冷暖,不用写而自然在读者的脑中补足,怎能不唏嘘?结构简单却平稳:用时间提拉一个人的一生,“五十八岁的阿三……三十天前……三天前……今天……”,如纲举目张,无所不容,却又清风送爽,无碍风流。语言精准、冷静,没有华丽的用词,只求简洁准确。没有煽情的渲染,只求冷静客观。王国维评词,当入乎其内,故有高格,出乎其外,故有高致。用之评此诗,也差不多吧。思想性不是火火的专长,然而在这首诗中,思想却显得老道而深刻,“在人群中失重”的何止阿三一人一事?“三十天前架在刀上,三天前飘在河上,今天之后挂在了墙上”,正是叵测难料的人生。
如今,重读此诗,心绪依旧难宁。掩卷思忖,可供印证、反思者良多。诗歌是什么?诗歌的语言是什么?现代诗歌应往何处去?
易安说词,别是一家。她所分辨的是诗词之别,她所在意的是音韵律动。而诗文之别呢?差别更大。大到因为结构完全不同,反倒不必谈了。现代诗歌因为不象古诗有固定的结构,诗文之别倒成了问题,要命的问题。
从《木匠阿三》中可以看到,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在形式上是沒有差别的(此处日常语言包括口语与书面语)。将诗歌断开,每一句话,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碰到。但是一整束,串在一起,顿时就离开了生活语言环境,自成为诗歌的语境。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诗歌语言在连缀中有其自身的逻辑性,它会让语言在平面上作画,而不象日常语言只是在线上描红。平面作画,重在尽意,尽意而不失其真。线上描红,重在真确,真确而不失其意。所以,诗歌语言尚简,尚纯,意尽为止。日常语言尚真,尚实,完整为止。
阅完一卷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林火火的诗歌语言之美。
“我想在秋天还未成熟之前,就把雨水关进你的掌纹”(《在路上》)。秋天的果实,雨水般的眼泪。雨水可以滋养果实,剖开果实,汁液又似乎是回味的浊泪。掌纹蜿蜒,仿佛水道,水道深浅,又象是命运的虚线。短短二十一个字,便把女性哀婉的情怀、决绝的爱恋,以及人生的况味与关照,压在一幅图景中表达了出来。一首诗,于此戛然而止。语尽而意不尽,意尽而情不尽。
“时间的刻刀,把少女砍成妇人,又让她充满感激”,“在我没发现的时候,杯里的一脸倒影已被吹皱”(《城》)。“砍”字,用的激烈。既符合刀的性能,又符合岁月的特征,同时,它还使得岁月之冷之无情,妇人之软之畏惧,在对比中放大越发强烈。冷漠者更冷漠,软弱者更软弱。如果诗歌到此而止,可以给“砍”一个精准的评语,但火火并未止语,接着又说“让她充满感激”,这句话,是个大反转,仿佛智者将妇人于镜前提起,猛然放到了人生的江湖上。于此,多了人生的反思,整首诗的境界又上了一层。“吹皱一池春水”的古韵,“杯中一脸倒影吹皱”的新意,各擅胜场,化用的很妙。既让人联想到古诗的余韵,从而有千古之思,又让人在皱纹之皱,水纹之皱中捉摸,人皱,还是水皱?风静水定,即使是惊喜,也是后怕。
“当它们(眼泪)跌落在相片上的时候,哥哥,你的眼睛也湿了。可是,你啊,却依然微笑”(《相思》)。谁的眼泪,只是“我”的吗?谁的微笑,只是哥哥的吗?此处,用了古诗文中相关的写法,两组事物性质相通,分别写,互相借,既节省了笔墨,又在传情达意中更添深一层的动荡与思想。含着眼泪微笑,微笑着流出泪水,何止“我”,何止哥哥,人生路上男男女女,或早或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。
这样的例子,不胜枚举。点染画面正是诗家的语言,不说人生而人生自在正是诗歌的本相。
火火写诗日短,人又顽皮,常说,我不是写诗,我只是玩。可是,艺术不正是游戏吗?因为玩,所以视角不与人同。因为玩,所以出语自然生新。
曾经给我看过一组短诗:《草鞋》,如果要私奔,就用芦苇将我们赤裸的脚印覆盖,不要归路。《唇语》,你的唇,落下。我闭上双眼,一只叫救赎,一只叫泅渡。《你来过》,那天,你在钉钉子。穿过蛛网的风,很简单。据说,这三首是她的初笔。真是令人惊叹。诗歌未必要写大智慧,哲学不是诗歌。诗歌未必要有罗浮宫,博物馆不是诗歌。诗歌如人,在神与兽之间,以和为贵;在爱与欲之间,以善为美。诗歌写到尽头,纯是一片人格,不是借用西洋或传统的道袍所能遮避的。
火火天性与诗道相通,可喜可贺。后天之力,假如在思想情怀上更进一步,结构布局上更上层楼,孰几可成大家乎?拭目以待。
- [04-01] 2025清明节放假通知
- [03-25] 太仓市娄东宾馆有限公司拟录用人员公示
- [03-20] 太仓市娄东宾馆有限公司拟录用人员公示
- [02-25] 太仓市娄东宾馆有限公司拟录用人员公示
- [02-14] 太仓市娄东宾馆有限公司拟录用人员公示
- [01-22] 2025年春节放假通知
- [12-25] 2025年元旦放假通知
- [12-11] 关于瑞宏精密电子(太仓)有限公司问题反馈的积分奖励公告
- [11-28] 太仓市娄东宾馆有限公司拟录用人员公示
- [11-13]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
- [11-01] 关于个人求职者反馈问题的奖励公告
- [10-18] 浮桥镇社会治理办公室招聘简章
- [09-27] 太仓阳光人才网服务器维护通知
- [04-03] 2025年太仓市上禾置地有限公司派遣人员招聘简章
- [04-03] 太仓泰纳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4-03] 利洁时(苏州)有限公司一线岗位招聘简章
- [04-02] 格莱德精密科技(江苏)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4-02] 鲍赫动力总成部件(太仓)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4-01] 苏州祝伟电器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4-01] 苏州芳科实业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4-01] 睿欧启富(苏州)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4-01] 鲍赫动力总成部件(太仓)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3-31] 苏州快燕筑巢房屋美化装饰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3-31] 苏州市富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3-31] 太仓文洋达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简章
- [03-31] 苏州诚和医药化学有限公司招聘简章